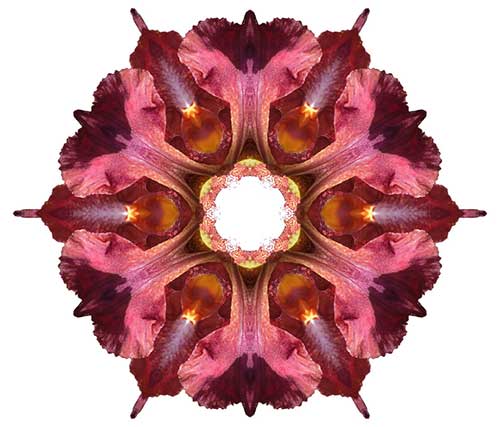佛教与美学
发布时间:2019-10-14 09:59:53作者:普门品在线网
我们所面对的对象世界、实现世界形形色色光彩照人的美,佛家从“因缘生法”、“诸法无我”的基本世界观出发,认为它们都是虚幻不实的,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、幻、泡、影,如露,亦如电”(《金刚般若经》),美这种现象也不例外。“色即是空”,必然逻辑地推导出“美即是空”。这便构成了佛教对现实美的基本态度。它可称之为“非美”。破美之有而说美之空,固然比执美为有的俗见高明一筹,但如果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,就有“带空”的迷执和愚妄,所以以“双非”、“中观”为思维方法的佛家进而主张“非‘非美’”。对“非美”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美的肯定,于是世俗人认为美的,佛家也认为美,这从佛教雕塑、绘画中佛像的“三十二大人相”、“八十种随形好”,佛经对佛国净土美好物像的描写以及佛教文学中对菩萨、比丘、魔女之美的刻划中可以见出。试看《华严经·人法界品》对比丘的描绘:
(善现比丘)形貌端严,颜容姝妙,其发右旋,如绀青色;顶有肉髻,身紫金色;其目长广,如青莲花;唇口月色,如频婆果;颈项圆直,修短得所;胸有德字,胜妙诗严;七处平满,其臂纤长,手指缦网,金轮庄严。无相而有相,于是产生了大量金碧辉煌的佛教建筑、雕刻、绘画,如敦煌、云冈、龙门三大石刻和壁画;无言而有言,于是产生了大量文学性很强、艺术价值很高的佛典文学,如《维摩诘讲经文》、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》。这样,佛教就从美的否定走向了美的建构,为人类创造了为他们所否定,为俗众所认同的千姿百态的对象世界的美,构成了美学史上独特的景观。如前所述,建构世俗美并非佛家的目的,佛教建构世俗美的目的在于“借微言以津(度)道,托形象以传真”(注:慧皎语。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义解论》。),使众生“睹形象而曲躬”、“闻法音而称善”(注:道高语。《弘明集》卷十一《重答李交卅书》。)。如《大般涅经》卷九《菩萨品》说:“诸佛如来……为令(众生)住正法(正道)故,随所应见而为示现种种形象。”佛家示观的种种形象、语言之美,不过是为引导众生“安住正法”的方便权宜之计。
佛教否定现实界的美和经验性(感觉性)的美,但并不一律否定美的存在。在佛典中,由佛教正面肯定的美大体有两类形态。一类是“涅”,一类是“佛土”。现实界的美属于依一定条件而生的“有为法”,因缘散则美空;感觉性的美(快乐感)是人类“无明”产生的“痴”,是一切烦恼与痛苦的渊薮,都不是真正的美。真正的美是不依任何条件而存在、超越对象世界的一切可视可听可感性、也超越主体感觉愉快之美的“涅”境界。“涅”是一种存在于修行主体内的“无为法”,一种以“寂灭”为特点的至乐心理境界。其间,“贪欲永尽,、恚永尽,愚痴永尽,一切烦恼永尽”,“寂灭为乐”(《杂阿含经》),“毕竟清静,究竟清凉”(《本事经》),具有“常”、“乐”、“我”(本体)、“净”四种美好的德性,一说具有“常”、“恒”、“安”、“清凉”、“不老”、“不死”、“无垢”、“快乐”八种美好的德性。这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美的大美,一种摆脱了世俗乐的大乐,可叫做“无美之美”,“无乐之乐”。
“佛土”又称“佛国净土”,是大乘所说的众佛居住的地方。相对于众生所住的“秽土”,诸佛的居所则是美妙无比的“净土”。关于“净土”之美,宋延寿《万善同归集》所引《安国抄》有“二十四种乐”之说,所引《群疑论》有“三十种益”之说。所谓“二十四种乐”者,“一、栏遮防乐,二、宝网罗空乐,三、树阴通衢乐,四、七宝浴池乐,五、八水澄漪乐,六、下见金沙兵,七、阶际光明乐,八、楼台陵空乐,九、四莲华香乐,十、黄金为地乐,十一、八音常奏乐,十二、昼夜雨华乐,十三、清晨策励乐,十四、严持妙华乐,十五、供养他方乐,十六、经行本国乐,十七、众鸟和鸣乐,十八、六时闻法乐,十九、存念三宝乐,二十、无三恶道乐,二十一、有佛变化乐,二十二、树摇罗网乐,二十三、千国同声乐,二十四、声闻发心乐。”(注: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》第三卷第一册第29页,中化书局1987年版。)常见的由净土宗经典所宣扬的西方极乐世界之美是众所周知的:在这个世界里,国土以黄金铺地,一切器具都是由无量杂宝、百千种香合成,到处莲花飘香、鸟鸣雅音。众生享受着“衣服饮食,花香璎珞,缯盖幢幡,微妙音声。听居舍宅,宫殿楼阁,称其形色高下大小,或一宝二宝,乃至无量众宝,随意所欲,应念即至”(《无量寿经》)。
涅之美与净土之美,是佛教直接肯定的美,它是对世俗之美的否定。
佛教本无意建构什么美学,它很少正面阐述美学问题,然而,佛教经典在阐发其世界观、宇宙观、人生观、本体观、认识论和方法论时,又不自觉地透示出丰富的美学意蕴,孕育、胚生出许多光彩照人的美学思想。佛教世界观讲“色即是空,色复异空”揭示了美的真幻相即,有无相生的特点;讲“梵人合一”、“物我同根”,“万法是一心,一心是万法”,揭示了“万物齐旨”,“美丑一如”的审美真谛;讲“有无齐观,彼己无二”,“内外相与以成其照功”,触及“内外同构”,“物我玄会”的审美观照方式;讲“心融万有”,“一切唯识”、“万法尽在自心中”,催生了“文,心学也”、“文不本于心性,有文之耻甚于无文”、“诗文书画俱以精神为主”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念;讲“识有境无”、“境假识真”,孕育了虚实互包的艺术意境论;讲“神我不灭”、“神精形粗”,哺乳了中国美学“遗形取神”的审美传统;讲善恶相报,奠定了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局。佛教的宇宙观栩栩如生地杜撰了三界与佛国、三千大千世界和世界的成、住、坏、空情景,显示了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。如形容宇宙空间的无限性,佛教先虚构了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层由低到高的境界,欲界由低到高分地狱、鬼、畜生、阿修罗、人、天“六道”,“天”道又分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乐变化天、他化自在天“六天”;色界在欲界六天之上,又分四禅十七天;无色界在此之上又分四无色天。从欲界的最底一道地狱上至色界四禅天的初禅天的梵天为一个世界,各有一个太阳和月亮周遍流光照耀,如此的一千个世界称“小千世界”,一千个小千世界称“中千世界”,一千个中千世界为“大千世界”。这样,一千个世界为小千世界,一百万个世界为中千世界,十亿个世界为大千世界。因一大千世界包含小千、中千、大千三种千,故称“三千大千世界”。三千大千世界(十亿个世界)是一佛土。佛教认为,宇宙并不是由几个三千大千世界,而是由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构成的。宇宙体积的巨大和空间的无边无际由此可见一斑。又,佛教形容宇宙时间的无限性,以“劫”为大的时间单位,它是不能以日、月、年计算的极长时间单位。从人的寿命无量岁中每一百年减一岁,如此减至十岁,称为减劫。再从十岁起,每一百年增一岁,如此增至八万岁,称为增劫。如此一减一增为一小劫。合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。成劫、住劫、坏劫、空劫分别是一中劫。合此四中劫为一大劫。大约一小劫为1600万年,一中劫为3.2亿年,一大劫为12.8亿年。每一三千大千世界都要经历成、住、坏、空四劫。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经历的变化时间也就无边无际。这种对空间和时间之无限性的想象能力,可能是一般的作家艺术家所不及的。佛教的人生观从“诸法无我”,“诸行无常”出发,揭示了“一切皆苦”的人生真谛,它传递给文学的,是“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”的郁郁感伤,是嗟老伤别、仕途失意的浓浓忧愁,是悲天悯人,爱人及物的菩萨胸怀。晋超《奉法要》指出:“何谓谓慈?慰伤众生,等一物我,推己恕彼,愿令普安,爱及昆虫,情同无异。何谓为悲?博爱兼拯,雨泪恻心……(注:同上书第一卷第20页。中化书局1982年版。(本文据佛教美学》一书前言增改。《佛教美学》,祁志祥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))
佛教本体论认为“言语道断”,故尚“无言”之美,又认为“道不离言”,故创造出“言教”之美,反映到美学创作上,就是“诗家圣处不在文字,亦不离文字”;认为“法身无相”,“般若无相”,故尚“无相”之美,又认为“业动因就,非形相无以感”,故创造出大量的像教艺术之美;认为“佛向性中作,莫向身外求”,“自身即佛”,不须依傍,影响到美学上,就是“问侬佳句法如何,无法无盂也没衣”,主张美在独创。佛教认识论崇尚般若空智和静观默照,所谓“不得般苦,不见真谛”,“圣心虚静,照无不知”,催生了美学构思论上的“虚静”学说:即“虚心纳物”、“绝虑运思”,并催生了一系列以静寂、虚豁、为特质的艺术创作;主张不假思索,直观现前,“现观”见道,直契“现量”,实际上触及审美的直观特征,具体说即审美的“现在”(现时、现前)性、“现成”(一触即成,不费思量)性,“现实”(真实)性;主张“顿悟”不废“渐修”,启发了人们对“诗道之悟”——灵感心理特征的认识;主张“离心意识参”、不主故常地“参”,涉及审美解读的无意识性和自由创造性。
佛教方法论以“无分别智”,这“无二之性”为“不二法门”,主张用“无分别智”的“不二之悟”,即“了无分别”的方式对待对象世界,孕育了中国美学整体不分、意象浑融的审美批评方式;崇尚双遣双非、无可无不可的“中观”之道,在“不即不离”的“诗家中道”上打下了浓重的烙印;从“外法不住”、“般若无住”出发说明“无住为本”,而灵活万变,不窘一律的“诗家活法”恰好与“无住无本”的“禅机”相类;崇尚“圆相”之美、“圆满”之美、“圆融”之美、“圆通”之美、“圆转”之美、“圆活”之美、“圆成”之美、“圆浑”之美、“圆熟”之美、“圆照”之美,形成了中外美学史上以“圆”为美的最丰富的奇观。此外,佛教戒、定、慧“三学”和“六度”、“八正道”等行为规定也构成了佛教徒行为方式的整体美学特征:这就是神定气朗、坚忍不拔、踏实精进、戒恶行善。佛教徒的行为方式一般人以为是消极的,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。佛教“六度”中有“精进”一条,“八正道”中有“正勤”(亦译“正精进”)一条,都是要求僧众勤勉苦修、积极向上的显证。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、忍耐力克除邪恶积习、进取无上妙道、谱写超俗人生,就是佛教徒追求的审美人生。(信息来源:香港宝莲禅寺)